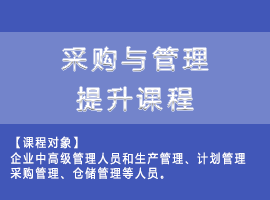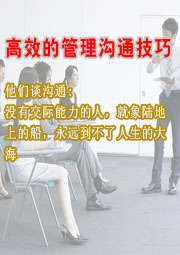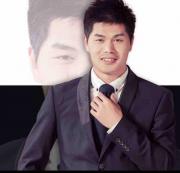国学的根本与源流
国学的根本与源流详细内容
国学的根本与源流
国学的根本与源流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甚至是最主要的标志。近年来的国学热是中国文化重新发扬光大的开端,“其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其巨大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必将对中国、对世界的发展有所贡献。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庞杂,其中精华是主流,糟粕也不少。国学一直都存在被误解误读的问题,一直都存在需要正本清源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国学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今天的国学热之中已经出现了很多乱相、怪相,这也必然。但这也对我们提出了艰巨的要求,要求我们能简单明了地说明博大精深的国学是什么。
国学的根本
所谓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中国文化。首先排除国故学就是国学的观点。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从古到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乱花渐欲迷人眼。究其原因,是不能提纲挈领地看中国文化,不能抓住文化的核心,文化的根本。真正的中国文化讲究整体性、系统性,整体系统中有一个根本,抓住根本就能纲举目张。
所谓“文化”,用西学定义的方式说,就是生命观和由生命观决定的价值观、认知思维方式,及由此所支配的一切生命行为。用国学的方式通俗地说,一个人,一个民族对自我、对世界的看法决定了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这就是文化。有人说,“国学就是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学问”,此话不错,但没有说到关键点、根本点上,应该说,因为中国人具有独特的“天人本一”的生命观,决定了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才使中国人成为独特的中国人。这就是“国学”。“人心惟危,道心微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出自《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心传就是华夏文明五千年薪火相传的火种,就是国学精炼的高度概括。可以说,读懂了这十六个字,就读懂了国学。
生命观是文化的根本,文化的“道”,其余部分是文化的枝节,文化的“术”。由此整体地看中国文化,系统完整,结构清晰,一目了然。
“天人本一”的生命观,这是一切中国文化产生的根源。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才能认清中国文化的本质与全貌,才能合理解释所有中国文化现象,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是伟大的,才能产生真正的文化自信,才能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对人类发展有所贡献的底气。抓住这个根本就能说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国学。
用现代语言说,国学精华中的精华,真正的精髓是“人学”,即研究“人是什么?”和 “怎样作人?”的学问,即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的学问,其核心是超越了巫术时代、人本文明时代、生命宇宙一体化时代的,中国人所独有的“天人本一”的生命观和 “致良知”的认知思维方式。
“国学”应该主要是指中国文化中关于“人学”的这部分。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学习国学的重点。其余部分可以归为“国术”,中国文化是一个“学”、“术”相互关联的整体。
过去 不用“人学”这个名称,古人所用的“心学”这个名称更准确。人与世界组成的这个整体就是生命系统。国学称之为“道”、“天”。从人的认知角度、属性角度来说,又称之为“心”、“性”。因此,国学也称为 “心性之学”、“性德之学”、“道学”。在“心学”里,“吾心即是宇宙”,因此,“心学”更是研究世界和社会的学问,也可以称为“天人之学”。
国学的生命观
国学是先进的,也是博大精深的、不容易理解掌握的。学贯中西、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辜鸿铭先生,在苦读了十五六年国学书之后,仍被大儒沈曾植揶揄:“你讲的话,我全懂,可是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需再读二十年中国书。”
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国学更是陌生的,不容易理解的。因为,国学的生命观和由生命观所决定的价值观和认知思维方式与我们现在接受的、通行的、来自于西方文化的人生观、世界观、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系统。因此,初学者看古人的国学著作往往不知所云,有读天书的感觉。要想进入国学的大门,首先要理解国学的生命观。
现代中国人的生命观受西方人的影响,人与世界分离,分为人生观,世界观。
西方人的人生观: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道德的高级动物。身体是人的主体。
西方人的世界观:世界是物质的。
西方人的价值观:人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生活。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满足生存需求第一,求知、审美需求排在最后。
国学的生命观相当于人生观+世界观。“吾心即宇宙”,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而一。”人与世界是一个整体系统。“我”的“能知”之“心”与“被知”之“天地万物”,不一不异,亦一亦异,“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这是中国文化最玄妙之处,最难理解之处,也是了解中国文化奥秘的入手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理解了这个天人本一的生命观,才能说国学入门了。
国学对“人”的认识:“人亦神,神亦人。人是未成神之神,神是已成神之人”。意思是人可以通过“致良知”超凡入圣。可以“知天”,“人心合道心”、也就是达到个体的“知”与整体的“知”的统一。“至诚如神”,“尽其心,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国学的价值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了解生命真相,获得生命“整体”的解放。了解了生命真相就可以“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
让我们看看古人所描述的理想的“人”是什么样的,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学的生命观。“古之真人,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这里的“一”,就是整体的境界,就是“人心合道心”的境界,就是《老子》第一章中“无欲以观其妙”的“致良知”境界。此时,“物我两忘”,“能(知)所(知)双泯”,只有浑然一体的生命系统在自动运行。“不一”,就是普通人的境界,就是《老子》第一章中“有欲以观其缴”的境界。国学并不是完全排除逻辑思维,而是既要用,又要认识到其局限性。
学国学就是致良知
为什么要学国学?仅仅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吗?国学把生命视为一个整体,没有“你、我、他”之分,“至人无我”。国学是开放包容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有人说,莱布尼茨根据《周易》发明了二进制,成为计算机技术的理论基础;有人说,某著名洋人社会学家说“孔子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始祖”;有人说,某著名洋人权威家说,“除了《道德经》,我们应该焚毁所有人类书籍”。按照这样的说法,墨子就是唯物主义的祖师,管仲就是资本主义的始祖。所有人类现象都可以在国故里找到根据。我们的文化自信就靠这些吗?这些恐怕都是不自信的表现。弘扬民族文化仅仅就是为了获得了个别洋人的一两句赞许而让个别国人自豪吗?中国人怎会如此浅薄?国学的价值又怎会如此微不足道?
学国学是为了从中找到作人做事的道德标准、行为准则吗?国学是不认可固定的“标准”、“准则”这些东西的,只认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要求该怎样就怎样。“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现在又有人大讲什么“斯文”,什么“温良恭俭让”,什么“仁义道德”,难道“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错了吗?真正的中国文化是该“斯文”的时候斯文,不该斯文的时候就不斯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为什么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因为龙善于变化,能应时而出,随机而动。如果只能培养不会随机应变的书呆子,那样的“国学”不学也罢。
学国学是为了更有学问吗? “没文化”的明白人太多了,“有文化”的书呆子也比比皆是,“老粗能办大事”,“百无一用是书生”。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真正的国学不在书斋里,而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只不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国学是全体国人的国学,不是读书人的专利。书斋里的东西应该是为实践服务的,还要能经受实践的检验。学国学是为了提高能力,不是为了积累知识。国学是实践的“学问”,讲究格物致知,讲究知行合一。国学是“实学”,要求“实证”。就是说,不仅要求明白道理,而且要求能亲身体验到。因此,古人要求“学而时习(实践)之”。要求“体悟”和“躬行”,要求“静处思虑,事上磨砺”。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庄子》
为什么要学国学?无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国学是先进的,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既负超世之见,又具入世之功。而且“大道至简”,国学用“致良知”这三个字可以概括。 “致良知”既是学国学的目的,也是学国学的手段,更是国学独特的认知思维方法。国学对人的要求只有“致良知”,而致良知足够让人终身学习。研究学习国学的意义正是把“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不自觉变成自觉的“致良知”。
从认知思维方法的角度来说,“致良知”通俗的说就是指人在“心态正常”的情况下,面对需要处理的事物,心中马上会自动出现一个“正刚好,无二择”的恰当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是“妙招”,不是逻辑推理能得到的,可比拟的。
“致良知”的“良知”一词出自《孟子》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还说“心之制,事之宜”。所以,致良知可以理解为“制心以宜事”。这是从功用的角度来说致良知的。致良知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更主要的、更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认知生命的真相,即弄清楚生命是怎么回事,这是最终极的“良知”。
这两个目的本来是统一的整体。但是,不强调后者,就会本末倒置。就不能站在生命整体的角度看问题,看自己,看世界,也就不能正确用心,即很难保持“正常心态”。因此,致良知首先要有对生命负责的态度。这样才能“志于道”, “以志帅气”,浩然之气充盈,积极主动,操存有素,不会临事苟然。同时,要知道,生命是整体的,不能只看到眼跟前,要超越时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穿透过去、现在、未来。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超越自我,“心包太虚,胸藏宇宙”。
“尽其心,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学国学就是要制心宜事,尽心知性,从而达到“知天”的目的。“知天”就是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天”、“道”这个生命整体大系统运动的一部分,我们的“心”,即我们生命的最根本的能力,我们的感知、觉知、悟知,运用正确,就能与“天”、“道”相符合,就能判断准确。这样就是“可以与天地参矣”。致良知,追求“己心”随时与“道心”相合,这是“国学”的核心。“人心惟危,道心微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学国学就是知心、用心、明心的过程。
知心: “心”与“外界”(包括事物,包括一切,物质的,精神的)不一不异,亦一亦异。“心”是生命的“能量”运动,是有力量的,用心不同,结果相异。“心”有“安定”的需求,心安才能理得。
用心:学而时习(实践)之,勿意、勿固、勿必、勿我。
明心:达到心明眼亮,气定神闲的状态。了解生命真相,获得生命整体的解放。
不要把国学神秘化、复杂化、理论化。学国学就是致良知,良知人人本有,遇事自会出现。但人往往被私见、欲望所蒙蔽,不能发现。所以,需要“致”,需要“明”,需要“见”。国学是无招胜有招,国学无招,你心自有妙招,你自心“明”了,良知不请自来,妙招自然有了。国学就是让人能够“明”心的学问。
中国早期的留学生或多或少都有国学基础,他们普遍有两个特点,一是学术方面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二是具有家国情怀,大都回来报效祖国。具有致良知的认知思维方式的人,往往视野开阔,博闻强识,才思敏捷,思想自由,性格成熟,品德高尚,干什么都能比其他人有优势。民国时期各种大师辈出的原因正是国学余脉的作用。
人贵在能“见事早,得计快”,临事“有办法”,“有思路”,有思路才有出路。人生最关键的出路是致良知。致良知能让人“见事早,得计快;看得见,抓得起”。致良知能让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致良知能让人随心所欲不逾矩。致良知能实现“自动化”,“不虑而得,不学而能,不见而明,不为而成”。毛泽东就是典型的具有致良知的认知思维方式的人。
致良知的最高境界是“知天”,“如神”,初学者不要急于求成,首先把握两点,站在整体的角度或旁观者的角度看问题和“虚心”(“我没有看法,等待良知判断”,避免先入为主),从日常工作生活入手,从做对具体的事开始,逐步提高。致良知贵在坚持,以恒为本。
国学的特点
正因为中西文化在生命观和生命观决定的价值观和认知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系统,国学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整体性
整体地、系统地、联系地看问题。“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而一。”“天之历数在尔躬”。“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样就有全局观,就能高瞻远瞩,站在整体的角度,看清问题的本质,避免私见的偏颇。
为什么有人“无为而尊”,有人“有为而累”? 为什么勤奋远远没有认知重要?成大事者,善假于“物”也。谋全局,谋万世,见趋势,顺势而为,点石成金。天道者,替天行道。忘我者也。人道者,闭门造车。自我者也。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诗作中有这样几句:“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送纵宇一郎》(1918年,25岁时所作)这是典型的“吾心即宇宙”之人的制身心之道。
致良知,“人心”合于“道心”,就会看清人间正道,就会发现天下一切皆可为“我”所用。这就是毛泽东能以“一人”之力扭转乾坤的奥秘所在。
聚焦当下,只论当下。
永远是面对现实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致良知”强调具体情况的理性把握,通过格物而致知。国学认为一切逻辑思维的产物——概念、规律、道德、是非乃至时空等等都是相对的,只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成立。唯一真理是“道要证道”,社会要向前发展,人要了解生命真相。这样就避免了思想束缚,拓展了思路。真正的“致良知”是“不分析”。
中国文化的“当下”,超越时空,穿透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参透命运,堪破生死。突破天人之际,出入六合,游乎九州。
中国文化绝不会有像西方人的天堂、上帝那样的,独立于此岸世界之外而存在的彼岸世界和彼岸神灵。因为,中国文化聚焦当下,只论当下。所以,国学中不可能有创造世界的第一因,即造物主的位置。也不会像斯蒂芬.霍金那样去探究时间的起源,更不会认可达尔文的进化论。国学大师南怀瑾说:“达尔文的祖先是猴子变的,我的祖先不是”。
为什么性格决定命运?为什么才子多落魄,红颜多薄命?为什么聪明美貌远远没有明白重要?国学对命运有着清晰的认识,对于怎样“革命”有着“科学”的论述。造化弄人人奈何,人弄造化出六合。毛泽东说人定胜天,史无前例。
国学既承认命运的存在,又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生者,乃所以善死也。”中国人把白事看成喜事,庄子鼓盆而歌,毛泽东曾对工作人员开玩笑说,我死以后,你们就开个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不知说生,不知恶死。中国人早就勘破了生死,超越了生死。
严格地说,“天人之学”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文化。真正的中国文化超出了天人范畴,“出入六合,游乎九州,是为独有。独有之人,是为至贵。”真正的中国文化是不能完全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道,可道,非常道。”
融会贯通,形象思维。
模糊概念,不一不异,亦一亦异。混沌逻辑,形象思维。
国学的很多内容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需要用心体悟、亲身体验才能理解,很难用概念解释。要求能克服非此即彼的概念性思维,能融会贯通各种概念的联系,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所谓“形象思维”,也有人称作“太极思维”,意思是像《易经》那样“思维”,《易经》就是典型的形象思维,“卦者,挂也”,卦像即心像,心像挂出来,一目了然。实际上,真正的致良知是“不思维”,即没有逻辑思维的过程,面对活生生的局面,自有良知出现。
古人小学要学《说文解字》,而汉字是象形文字,通过“说”四五百个 “文”(基本文字单元,部首),就可以掌握绝大多数汉字的来龙去脉(解字)。这样,不仅记忆牢固,而且理解全面。古人以诗教启蒙,而诗是“心境”的写照,蒙学即开始培养人在无意之中用心,陶冶性情。这样,通过学习“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比较容易地打下坚实的文字基础,所以古人读几年书就几乎都能出口成章,吟诗作对。
正因为一切逻辑思维的产物都是相对的,国学没有所谓“理论体系”,真正的国学经典都是前人致良知时的自心描述,即所谓“述而不著”,国学经典都是使人心“感而遂通”的工具。“感而遂通”,就是心灵感知万物而通“天”、“道”,即在平常日用之中致良知。因此,学习国学要 “体悟”和“躬行”。而不能按图索骥。如果采用西方哲学逻辑思维为主的方式,想找到学习国学的规定步骤、固定模式是不可能的。如果想从国学中找到现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百战百胜的法宝,那就是误入歧途了。国学最反对的就是教条主义。
我们不认为当代人类的所谓“哲学”,全部是垃圾,但全是在“亚里士多德陷阱”之中,是毫无疑问的。要把中国文化删简之后,庸俗化之后,纳入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思维的思想体系,只能是让人啼笑皆非。“新儒家”、胡适、冯友兰等很多“哲学家”一直都在干这样的事。中国古人是文史不分家,文以载道,史以印心,哪有什么现在的“文史哲”的哲学啊?我们不反对研究应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是说当代人类的所谓“哲学”,试图解决“道”的问题,却达不到“道”的认识高度,只能归为“术”的范畴,只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成立。而且,很大一部分“哲学”是哲学家的“意识游戏”,对人们的生活、对人类社会没有任何影响。一些哲学家根本不知“心”为何物,更没有“用心”的实践体验,就敢生搬硬套地把“心学”说成“唯心主义”,真是无知者无畏。
国学的源流
值得提醒的是,西方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古代人也好,现代人也好,之所以不能完全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的认识仅仅局限在人本文明时代的范围,以自己的有限的见识理解解读国学,而国学是超越了时代的。正所谓“井蛙不可以语於海,夏虫不可以语於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比如,有人拿着人本文明时代的西方“哲学”的概念、逻辑、理论生搬硬套地解读源自巫术时代的《易经》,这样的事本身就有点滑稽,遑论结果。《老子》《庄子》都是“出入六合”的著作,视野只在“六合”之内,如何解释得清楚?
文以载道,史以印心。在国学看来,历史即是我“当下”之“心”的一部分。历史是用来“明心”的。让我们跳出人本文明时代,站在生命整体的角度,粗略地梳理一下国学的发展脉络,这样或许可以对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国学有所启发。
从生存与发展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大致经历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时代,刀耕火种的农耕文明时代,机器轰鸣的工业文明时代,现在这种以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为主的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经历原始社会用了超过一百万年时间,农耕文明大约用了一万年左右,工业文明到现在大约五六百年,后工业文明大约几十年到一百年左右。人类社会是加速度发展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从对世界认知的角度看,人类经历了“名物两可”的巫术时代,“名物两非”的人本文明时代,最终要发展到“名物一如”生命宇宙一体化的时代。如果说原始巫术时代是“唯神”主义,现在的人本时代是“唯物”主义,将来的生命宇宙一体化时代很可能将是“唯知”主义。1943年,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中有这样一段:“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已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人本文明”之前,人类社会经历了巫术时代。巫术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名物两可”,即类似“咒语”的现象。那时人们的感知极其不统一,极其不稳定,幻听幻视普遍。那时的人类社会法术横行,咒语满天,人们根据“法力”高低决定统治权。当一个统治者失去法力的时候,另一个法力更高的人把他杀死,取而代之。最典型的巫术文化是古埃及的法老时代,欧洲的基督(天主)教普及之前的原始宗教时代。
那时的人类直观感觉自己与外界是一个整体,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 ,感觉外界是从自己心中流出的,万物有灵,类似《旧约》的上帝创世纪。
虽然原始人不同程度的有“心想事成”的能力,但他们把身体当成了自我,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身体的生理需求,统治者穷奢极欲,其他人照样过悲惨的生活。现在还可以看到金字塔、南欧的原始宗教神庙等巫术时代的建筑遗迹及法老咒语等巫术时代的记载。
中国史前文化也经历了类似的时代,直到夏商时期用活人祭祀、陪葬还是很普遍的。《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在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的过程中,双方先由巫师作法,那些被巫术呼唤来的暴风雨曾使黄帝军队陷入困境,后来黄帝也依靠巫师的法力才转危为安。
在三千年前的人类中,“心想事成”是生命的本有功能,上古群魔乱舞时代的出现,也即巫术图腾时代的出现,即是由于人类在不了解生命真相的情况下的“心转境”的乱用。
原始文化与现代文化不是也不可能是截然分开的,必然有一个交叉过度的过程。即便到了今天,全世界范围内普遍还有巫术残留。
现在的人类世界观,是“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实际上,直到今天,除了真正掌握了国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之外,很多人还是只“对立”,并不“统一”。
怎样“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具有统一性,世界是物质的”,“精神一种特殊的物质”。马克思还在《伦敦手稿》中提出过“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命题。“人的本质力量”(国学称为“道”,生命本体)只有“对象化”(表现为一定的载体)之后,才是可知的。人、动物、植物乃至整个宇宙,凡是“被知”,皆是人的本质力量(生命、道)的对象化,都是生命的载体或存在方式。这与“我心即宇宙”有异曲同工之意。毛泽东在上述批语中还有这样一段:“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这就是“统一”。如果人们能用国学思维,融会贯通,不被“物质”、“能量”、“力量”、“精神”、“道”、“天”、“人”、“生命”这些概念限制,应该能够理解这个“统一”。说的再通俗一点,世界的一切,包括人的精神、身体,具有同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物质”,国学称之为“道”、“生命”。理解这个“统一”对理解国学的生命观很重要。
我们今天的时代之所以称作“人本文明”,是因为这是“以人为本”的时代,“人”这种生命的“高级形态”有物质需求的属性,“物质”对人本文明时代的社会发展显得特别重要,所以这是唯物主义的时代。这也是从这一时代人类认知的特点。
相对于巫术时代, 现代文化是“名物两非”的时代,即“名”与“物”是分离的。一般法术、咒语不再起作用,人类感知比较统一,十分稳定,很少幻听幻视。比起原始文化,现代文化无疑是很大的进步。但人类进步的脚步一定不会在此停下。“名物两可”、“名物两非”,玄学巫术、科学技术本质上都是“美之为美”,从实际效果来说“名物两非”更容易使人们认幻为真。将来,人类跨越“名物两可”、 “名物两非”的时代之后,将进入 “名物一如”的时代。
国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国学是了解了生命真相的,一方面坚决抛弃“名物两可”认知阶段的咒语迷信的盲目性,一方面又尽力使人们从“名物两非”认知阶段的温柔陷阱中脱离出来。国学之所以不容易理解,就在于人们只相信自己的直观感觉,根本没有意识到人类认知方式的局限性。
一般人们凭直观感觉认为先有“物”后去“知”,不管去不去“知”,“物”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一个统一的、固定的时空框架。国学认为在同一个“知”中,“知”和 “物”是一一对应的,不存在谁先谁后,谁派生谁的问题,而且没有时空框架。时空是“心理错觉”。
我们现在所谓的“知”的过程,实际上是“名”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念:感受,第二念:存留、判断、推理,形成概念。
第一念:感受,可以称为“镜照”。是说第一念就像照镜子一样,镜子里面的图像是镜子外面的物体的直接反映,二者肯定是一一对应的,同时产生的,没有先后,也不存在谁派生谁的问题。因此,人的认知能力——心——能知之心,也称为“心镜”。理解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需要提醒的是,“镜照”的 “知”肯定是最准确的。
“名”是指第二念,是指“心镜”里一有图像,人不由自主的会对这个图像进行存留、判断、推理,形成概念。这是人的属性,是人就会这样做。否则,对人来说,这一“知”就没有完成。也就没有完成生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问题是,加上这人为的第二念之后,“知”肯定是不准确了。因为,第二念早已脱离了第一念,用物理学的概念,相当于进入了另一个惯性参照系,按照相对论观点,不同惯性参照系之间没有统一的时间,当然也就没有统一的空间。用国学的话说就是进入了另一个“当下”。
人们可以仔细体验自己的认知过程,看看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一个事物,心里先有一个直观图像,然后心的注意力马上脱离了事物本身,转移到图像上了,然后再根据心中原有的概念、观念、规律等对图像进行对比、判断、推理,完成对“物”的确认,心才能安定下来,这个“知”才算完成了。把第二念这个经过“人工处理”过的“认知”当成了第一念的认知,这个知“知”肯定是不准确了。这也是时空“心理错觉”产生的原因。
第二念这个“人为的”逻辑思维过程,在《道德经》中说的是 “美之为美”,“善之为善” 的过程,在儒家孔子说的是“自、意、固、必”的过程,在《圣经》中说的是 “人类偷吃禁果,有了分别能力” 的过程,在佛经中说的是 “知见立知” 的过程。
就是说“名” 的过程是用概念对“物”命名的过程。“物”不是永恒的“客观存在”,而是随着命名而一起产生的。一切概念、观念、规律、定理、学问、道德等都是人心对“镜照图像”进行逻辑思维的产物。都不是永恒的“真理”。都只是“道”的显化过程,都是“道”的能量运动,都只是“心”的能量运动。
今天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都在倒溯这个过程。这也是“道证道”的过程。
从“道”到“知”、“物”、“名”三分,三者是绝对同一的。因此,“物”就不是没有生命的,“名”也就不是没有力量的。“心”动之时“物”也在动,只不过这种动,很可能给人造成一种心理错觉,以为只是“物”自己在动,而“心”莫过是旁观者。正是因为人们不知自己的“心”与“物”同动,错认是 “物”的自动, 但又永远说不清“物”动的原因,便会认为是神在起作用,其实还是自己的“心”在动。把心与物截然分开的人类,不了解这一点,被自己的心理错觉所迷惑,以为是自己心外的一个神或一个物驱动了物,这便是一切有神论无神论思维的来源。一个名迷于神,一个迷于物。迷于神者,自然想与天沟通,迷于物者,自然想探究物理。这就是玄学巫术科学技术的来源。
面对认知局限性的人类究竟该怎么办呢?古圣先贤各有各的办法,各有各的高招。老子“两个沒身不殆”:“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既得其母(能知),以知其子(被知)。既知其子(被知),复守其母(能知),没身不殆”。耶稣“三个世界划分”:把一个世界给人们划分为天堂、人间、地狱三个世界,让人们按照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原则,只管研究人间世界,不许讨论上帝的事情。这样人们就会因为向往天堂而不迷恋世间繁华,因为怕坠地狱而不敢为所欲为。”孔子“四个勿”:“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释迦“五蕴皆空”:“色、想、受、行、识五蕴皆空”。他们的方法虽然有详有略,认识程度也参差不齐,但都和“致良知”是相通的。
华夏文明的“名非时代”大约始于黄帝时期。史书有关于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的传说记载。因此,黄帝被奉为华夏人文始祖,但直到夏商时期巫术仍然十分盛行,到了西周基本完成了过渡,正式进入了现代文化的“名物两非”时代。
自黄帝肇始,经过尧舜禹,商汤伊尹,周文王姜尚,基本进入了人本文明。文明的转型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变革。夏商以前的文化据传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现在能见到的只有易经的一种,即《周易》。《山海经》从内容看是记载巫术时代的,可能是后人根据传说整理的。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完成了人本文明的文化框架的搭建。其中道家超越了巫术、人本文明,生命宇宙一体化,站在生命总体的高度阐述生命的体用,即“道德”(此道德非彼道德。“道”指生命之“体”、“本体”,就是生命的根本、本质。“德”有“德性”、属性的意思,是指“道”根据其“道要证道”的属性——也就是《易经》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表现出来的、我们能具体感知到的种种现实现象,即所谓生命之“用”。),因此被称为“道德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诸子百家中的主要六家“有省与不省耳”。最“省”的,即最明白的就是道家。
司马谈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家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唱而人和,主先而人隨。”
司马谈这段论述未必全面,却很精彩,对儒道两家的表现描述得十分准确。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
道家、儒家对中国对影响最大,后世大多外儒内道,外儒内法(法家源自道家)。中国历史宛如一出木偶戏,孔子在台前表演,老子在幕后操纵。于是,人们只见孔子,不知老子。正如伟人所说:“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孔子成了中国文化的形象代言人,现在世界各地都在开设孔子学院,国内也有很多人以为国学就是孔孟之道。
《论六家要旨》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觽多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阴阳家,易经加阴阳五行也,源自巫术也。历史最悠久的学派之一,过去对中国影响很大,中医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理论上的,二十四节气现在也在应用。不要“美之为美”,谈巫色变。巫的原意是与天沟通,关键是怎样理解“天”。巫术时代所理解的“天”就是“神的意志”。后来的儒家、史家、医家等都源自巫。“巫”既然存在,研究中国文化就不能视而不见。玄学巫术和科学技术都是人类探求生命真相所用的手段。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唯大道不易,其余皆可易也。《易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易有三易,或者说,易有三意:不易,变易,简易。道不易;术变易,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操作简易,致良知。
到了西汉,汉武帝刘彻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注意,是“术”,而不是“道”),结束了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天子成了神圣的代名词,通天教主。儒家沦为通天教主的御用意识形态工具。儒教、孔教、礼教、名教都是通天教,实际起到了宗教的作用。官方的帝王文化,实是图腾文化的遗迹的通天教主文化;神学宿命论、神圣道德论是其基本的思想支撑。民间的落后保守的小农自给自足的封闭文化;神学宿命论使其迷信,神圣道德论使其愚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都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这样的文化有两尊神,天子与孔子。天子神武自不必说,至于孔子,日本人远藤隆吉说: “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处于人表,至岩高,后生瞻望弗及,神葆其言,革一义若有刑戮,则守旧自此始。故更八十代而无进去者,咎亡于孔氏。祸本成,其胙尽矣。”
华夏民族汉唐以前推行道家、法家思想,社会发展比较正常。汉唐风韵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盛唐时期,思想开放,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对外包容,重视军事,发展教育。
自武则天之后,中国文化江河日下,汉唐雄风不再。自宋赵匡胤兄弟提倡“开卷有益”开始,脱离实际,重文轻武,尤其是朱熹理学成为官方道统之后,假道学横行,心学大坏,文化偏离了正轨。在丛林时代,整天的满口仁义道德不是自欺欺人吗?
人们变得道貌岸然,萎靡不振,沉溺安乐。虽然有一大堆兵法,多数时候还是打不过没有兵法的北方游牧民族。不尚武,不堪到曾经两次遭受少数民族统治共三百多年,尤其是被总人口不过几十万的满族人统治了二百多年。
历史上,华夏民族建立过辉煌的大唐盛世,也有过卫青、霍去病、朱棣逐匈奴于漠北的武功,有过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的对外交往。但总体来说,由于通天教主们的自私与无能,“孔孟之道”的影响,加之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华夏民族勤劳智慧,但也不务实,不尚武,不思振奋,固步自封。
这使得中国社会两千多年一直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兴久必衰,衰久必兴;兴则沉溺于安乐,安乐则衰,衰则忧患,忧患则兴的怪圈里轮回流转。因此,文化只有像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一些表面形式的变化,而对文化本质“道”的理解,大多数时期内的多数人都是误解的。清末,工业文明的浪潮袭来,古老的帝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时不知如何应对,连遭列强痛打,以至于到了亡国的边缘。
这样的“中国文化”较之以掠夺为特征的西方文化看似是文明得多,但终是没有与巫术图腾文化彻底割裂。就中国来说,一直局限于“通天教主——自耕农”文明的小圈子,看似温馨,实际上道、儒、释文化却都被大大扭曲了。进入二十世纪,想再前进一步,也已经是寸步难行了。多亏西方人的洋枪、洋炮在背后击了一猛掌,这才有了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二十世纪的大进步,大改组,大换血。
我们应本着“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的目的学习国学。应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看历史。对于自己的文化历史,我们不能只大而化之地冠以“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了事。古往今来,多数时期的多数国人对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认识是模糊的,不清晰的,甚至是混乱的。具体表现有:
最粗浅的认识,以为孔孟之道、阴阳术数、图书印玺、医方辞赋、民俗节气、百家讲坛、昆曲京戏、亭台楼阁等等这些文化的表面形式,就是中国文化的全部,而不知表象背后的根本。更有甚者,把《弟子规》《曾国藩家书》这样的东西奉为信条。
中国文化应有尽有。天人之道,实用技术,巨细皆有;玄学巫术,科学技术,虚实俱全。不明道术之要妙,不能提纲挈领,中国人披褐怀玉,拿着金饭碗讨饭,可不哀哉?
最根本的混乱在于对人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孔子说,畏天命,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他的天是要祈祷的。董仲舒说,天人合一。他的人与天是要合的。天人本一何须合?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最终认识也只到天人之际。司马迁与他的老师董仲舒基本同一水平。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荒谬!人欲即是天理。
我们不去纠缠他们的文字,实在是这些人对天、人是怎么回事没有搞清楚。加之他们的影响很大,给人们的认识造成了极大混乱。孔丘的所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是中国文化的糟粕。张载的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简直就是酒后狂言,被马英九这样的哈佛博士引用不足为奇,很多“国学大师”也拿来过嘴瘾就说明问题严重了。
很多儒家不明生命的真相,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天天讲“明明德”,没有多少人能讲清楚什么是“明德”。结果把自家人也误导了,后来“明德”就变成了“高尚的道德”。最后,儒家只剩下“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孔孟之道”了。岂不妙哉?
曾国藩、蒋介石就是这种中国文化糟粕的受害者。曾国藩是典型的小人儒,而非君子儒。他当时对世界和国内局势是了解的,本来有机会、有能力推动中国进步,王闿运和一些部下也劝他“问鼎”,可他不为所动,一心只想保全自己的名节,全然不顾国家前途。所以,联想到当时的世界形势(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都还没有开始)和之后的中国百年沉沦,有人说他是民族罪人,也不为过。蒋介石虽是基督徒,却一生热衷于中国文化,推崇王阳明,信奉曾国藩,嘱咐钱穆著《清儒学案》,并且一直坚持按照儒家要求修身不辍。可惜,他误入歧途,走的是曾国藩的老路,言必称“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不知道“明明德”就是明心,就是致良知,最终也没能迈进“阳明心学”的大门。成了“见事迟,得计慢”、“总是慢半拍”的国学反面教材。
按照国学的思维方法,只有具体的儒家,没有抽象的儒家。可以肯定,儒家孔孟对“天”的理解肯定不像老庄那样透彻、究竟,尤其是孔子,还有巫术时代影响的痕迹,但也肯定不是完全像巫术时代的“老天爷”,即有“人格神”在主宰世界。孔子说人可以知天命,孟子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真正的儒家是孔孟的儒家,不是董仲舒、程朱的儒家,真正的程朱,也不是有些人理解的朱程。但不管怎样,事实上儒家对中国文化形成了误导。
儒家只有到了陆九渊,王阳明才算步入了天人之学的正轨。
道家的遭遇也没有好到哪里,“无”被解读为“虚无”、“什么也没有”,“虚无”在国学里根本就不存在,也没有意义。“无为”被理解为什么也不干,“无为”的本意是“我”无为。意思是 “我”为与不为要看“天意”。天不让我为,“我”不为所欲为。天让我为,我为了,也不是我为的,是天为的。如果天让我为,我却偏偏不为,那就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这个“天意”一点也不神秘,实际就是就是“忘我”,即认识到天人本一,“我”能站在整体角度看问题,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好好色,恶恶臭”,慢慢的就会体会到“天意”。
再比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小学造诣颇高,对国学著作的字面意思理解很准确,但明显地对字面之后的真正含义无感。他考证出“哲”是“知”的意思,却认为这个意思太简单,不能表达“中国哲学”的深邃。他不知道,真正的中国文化根本就不研究西方式的逻辑思维堆砌的所谓“哲学”,却处处都是中国式的具体感知的“知”学。“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在国学里“知”就是一切,“知”正是国学研究的重点。他不知道,大道至简,都在平常日用一“知”之中,一“知”就能与天地同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对真正的中国文化的误读,与儒家的误导(或者说人们误解了真正的儒家)有关,当然也和时代的局限性有关。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学确实博大精深,不易理解掌握。著名教育家,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一文中说:“明明德之义,释以今语,即为自我之认识,为自我知能之认识,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而执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尽,过此即须学子自为探索;非执教者所得而助长也。”这是一个国学过来人的真知灼见。
中国文化本身是先进的,但是也是不容易理解和掌握的。只有到了今天,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现代物理技术,通信、网络等信息技术,基因工程、克隆等生物技术作基础,让多数人掌握真正的中国文化才有了可能。这其中,毛泽东和近代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示范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国学发扬光大的有利条件。
国学的现实意义
从终极意义上说,学国学的目的是了解生命真相,确实只有求知与审美需求而没有功利要求。但怎样实现这个目的,过去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董仲舒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谈功利如何“好好色,恶恶臭?”如何检验效果?只能以人为的“道德”“教条”为标准,这样先入为主能致良知吗?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本意可能与孔子的“克己复礼”一样,都是说要克服私见,与整体相符合。但在实际方法上,千百年来朱熹等儒家确实抽象地认为人具有“本善”的“义理之性”,提倡 “复性”。制订了一系列所谓符合“天理”的人伦规范,如“三纲五常”等,并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具体的生命个体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彻底否定人性,彻底否定人的正常生活。这些都是脱离了具体的“当下”的、抽象的、人为的、理想化的方法,其效果已被证实。
真正的国学永远是面对现实的活生生的“当下”,永远是不离当下用心体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立足现实,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功利不是国学的最终目的,但具体到处于人本文明的后工业时代的“当下”,国学与功利是联系在一起的。当年西学东渐风头正劲的时候,辜鸿铭先生顶风进行东学西渐,想用温良敦厚的中国文化教化侵略成性的西方人,除了在刚刚遭受了一战战火涂炭的欧洲引起短暂的反响之外,没有太大效果。除了辜先生所宣扬的是儒家学说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国力衰弱。什么时候中国人均DGP超过美国,中国文化就被世界认可了。所以,当下发展是硬道理,而认知是第一发展力。
就个人而言,今天的很多人所思所想大都集中在生存竞争所带来的压力上,仿佛内心只有一个声音:“要生存,要比别人活的更好”。难得认真想过关于“人学”的问题,现在很难从国人身上看到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孔颜之乐”、庄子“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逍遥自得”是什么,很难理解“天堂”其实就在人间。认为这些东西是虚妄不实的,岂不知这些都是能实实在在体验到的,岂不知如果掌握了真正的国学能使你的发展如虎添翼。朋友,你是否想过为什么毛泽东早年能“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否想过为什么毛泽东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能带领中国人重新站起来?这其中,优秀的的中国文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国人最需要的学习是学习国学。实际上,国学既负超世之见,又具入世之功。二者是统一的。即便只从发展的角度看,也是工夫在诗外。如果只就发展论发展,就看不清发展的本质,只能被表象所迷惑,如何看清发展的方向与道路?只能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中国自强图新之路的探索,只有到了掌握了真正的中国文化精髓、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灵魂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才看清了他们各自面对的具体“当下”局势的实质,为中国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与道路。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大惑者,大愚者,大有人在。知其愚,知其惑,不知其所愚,不知其所惑,终究还是不知其愚,不知其惑。知行合一,知行本一。能知不能行不是真知,知而不行,于事何益?
超世之见:“以方内为桎捁,明所贵在方外也。夫游外者依内,离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无以天下为也。是以遗物而后能入群,坐忘而后能应务,愈遗之,愈得之。苟居斯极,则虽欲释之而理固自来,此乃天人所不赦者也。”只有掌握国学的生命观,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例如,所谓互联网思维,不过是宇宙生命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的认知特点而已。互联网时代更能发挥“致良知”的优势。
入世之功:当今世界发展变化之快前所未有,唯有致良知的认知方式才能与之相适应。今天人类的思维水平,基本上还是孩子式的、个别的、单向的、静止的、模块化的、孤立的……应该指出,一百多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是力图避免这种单一逻辑思维认知方式的弊病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是在进入中国之后,才初步取得了这样的效果。这与第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着丰厚的国学底蕴,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现在大多数人所使用的西方式的孤立性和概念性的思维方式转变成国学的系统性和具体性的致良知认知方式,人的能力将有质的飞跃。了解了国学的生命观再去搞科学研究,生产经营,社会活动,人的看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将会有根本转变。所以,今天要发展必须学习掌握国学,必须致良知。
发展是硬道理,认知是第一发展力。看得见,才能抓得起。一个人,能不能发展,首先看他能不能“见事早”,见事早则“得计快”。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能不能发展首先看其能不能认清历史发展的潮流,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脉搏。
中华民族要想对世界有所贡献,就要求对世界局势的理解能超越时代。要想超越时代,只能从人类生命大解放的角度看历史发展潮流。人类生命大解放经历了蒙昧时代,巫术时代,人本文明时代,现在正处于从人本文明时代向生命宇宙一体时代过度的前夜。
中国人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不思振奋,因为我们有优秀的文化。我们有正确的生命观,有先进的致良知的认知方法。悠久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国学案例。每个中国人身上都保存着中国文化的基因。这是我们的优势。
作为中国人,应该了解学习中国文化。最起码应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心想事成”将有可能变为现实。随着生物技术,基因技术,生命科学的发展,人类对生命的理解将进入新的阶段。试想一下,医学和人造器官技术是否可以发展到像修理汽车一样修理人体?如果出现克隆人,如果能够任意修改人的基因图谱,对人,对生命的认识能不改变吗?
霍金担忧人工智能将淘汰人类。从发展趋势看,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现在电脑已经可以在人类最复杂的智力游戏——围棋上与人脑一决高下。拥有自主学习功能的机器人将很快达到能完成人类大部分工作的程度。果真有霍金所担忧的那么一天的话,才是检验什么是真知,真理的开始。即便人类消失了,生命、真知永存。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存在而已。
真正的中国文化能让我们看清人的本质,世界的本质,真正的中国文化能让我们看清科学技术的本质,玄学巫术的本质。真正的中国文化能为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为即将来临的文明转型指明方向和道路,真正的中国文化可以为人类生命大解放指明方向和道路。
掌握了真正的中国文化才能处变不惊,气定神闲。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张景利老师的其它课程
- [潘文富]公司规范化改革的前期铺垫
- [潘文富]为什么店家都不肯做服务
- [潘文富]厂家对经销商工作的当务之
- [潘文富]经销商转型期间的内部组织
- [潘文富]小型厂家的招商吸引力锻造
- [杨建允]2024全国商业数字化技术
- [杨建允]2023双11交易额出炉,
- [杨建允]DTC营销模式是传统品牌数
- [杨建允]探析传统品牌DTC营销模式
- [杨建允]专家称预制菜是猪狗食,预制
- 1社会保障基础知识(ppt) 21255
- 2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ppt) 20330
- 3行政专员岗位职责 19114
- 4品管部岗位职责与任职要求 16373
- 5员工守则 15537
- 6软件验收报告 15460
- 7问卷调查表(范例) 15204
- 8工资发放明细表 14660
- 9文件签收单 14315